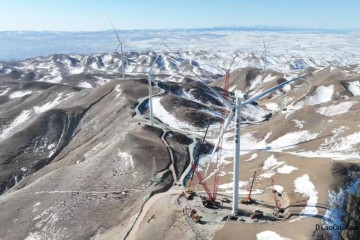中交長沙建設職工文苑柯基的曠野與屋檐 晨光熹微,當工地還未完全蘇醒,食堂的燈光已經率先點亮黎明,裊裊炊煙如輕紗般升起,后勤人員開啟了靜默而又忙碌的一天。
時光總給舊憶鍍上暖光,哪怕當年的顛沛像根刺,扎在狗生里。我是一只小柯基,一場突如其來的車流,把第一任主人的味道從鼻尖徹底卷走了。我在街角嗅過千百次她的氣息,我沿著熟悉的巷口跑了三個秋,嗅過無數片梧桐葉,沿著熟悉的路燈跑斷過腿,可回家的路像被雨水沖散的腳印,連殘影都抓不住。那時候才懂,世間的相聚是猝不及防的饋贈,離散卻是無聲無息的掠奪……就像人類說的,有些告別,連 “再見” 都來不及嚼碎咽下。
后來便在流浪里學會了生存。天是藍被子,地是軟褥子,餓極了和另一只流浪狗“阿汪”搶過垃圾桶里的骨頭,也跟一只叫“阿喵”的野貓較過勁。它大概瞧我腿短,弓著背就撲過來,我沒等它站穩,縱身把它按在泥里。阿喵“喵嗚”求饒時,我忽然盯著自己沾泥的爪子發愣——從前被主人捧在手心時,我連拖鞋都舍不得咬,如今竟能把野貓按在地上。人類說“弱肉強食”,原來流浪的日子會把軟毛磨出硬刺,連眼神都得帶著點鋒芒。
遇見小賈是在一個暴雨天。烏云壓得像要塌下來,閃電劈開天空時,雨珠像碎玻璃砸在背上。我踩著小短腿在水里淌,汽車駛過濺起的泥花糊了滿臉,路過的人笑著指我:“這小短腿跑得倒急。”正縮在廣告牌后發抖時,聽見有人笑著對我說:“你好呀小柯基,怎么淋成落湯雞了?”抬頭看見個戴安全帽的男人,他沒繞開我,反而停了停,安全帽下的眼睛彎成月牙——那是我流浪以來,第一次在人類眼里看見“不嫌棄”。
我悄悄跟在他身后,看他走進紅頂白墻的院子。這里的人都戴著安全帽,圖紙在桌上攤成山河,有人對著對講機喊“安全支護要加緊”,有人蹲在路邊啃饅頭時還盯著施工表。后來才知道,他們是架橋修路的人,要把陡峭的崖壁鑿成通途,把湍急的河谷架成橋梁。而那個對我笑的男人,大家都叫他“小賈”。 我在他宿舍門口蜷了三夜。第三晚他加班回來,借著路燈看見我打結的毛,忽然把我抱進衛生間。熱水沖掉泥垢時,鏡子里晃出個圓滾滾的影子——原來我還能這么干凈。他指尖蹭過我耳朵時,我忽然想起從前主人給我梳毛的溫度,喉嚨里忍不住發出“嗚嗚”的哽咽。
項目部的日子像泡在溫水里。小賈的板房里總飄著雞胸肉的香,工友們路過時會蹲下來揉我腦袋,說“這小短腿是咱們工地的吉祥物”。我總趴在他辦公桌下等他畫圖紙,看臺燈把他的影子投在墻上,像棵沉默的樹,也總在他加班到深夜時,悄悄把腦袋擱在他鞋上——他會停下筆,摸出火腿腸掰成小塊,指尖沾著圖紙上的墨痕。
日子慢得像熬粥,可粥里有火腿的咸香,有小賈打盹時的輕鼾,有工友們說“通車了就能回家”的期待。我看著工地從一片荒坡長出橋墩,看著燈光從黑暗里一點點透出來,就像看著日子慢慢長出形狀。
直到那天遇見小黃。幾只野狗闖進院子時,我梗著脖子要護地盤,卻被按在地上啃耳朵。是小黃沖過來的,它跑過的時候,草葉上的露珠都跟著晃。它把野狗趕跑后,蹲在我面前甩尾巴,眼睛亮得像浸在溪水里的星子——那一刻我忽然明白,安穩日子過久了,心里總會長出點野芽,想跟著風跑向曠野。
小賈把我抱回去時,我還在回頭望。他給我涂藥膏時,指尖的溫度很輕,可我總想起小黃跑過草地時,四蹄踏碎陽光的樣子。后來他開車帶我去兜風,風從車窗灌進來,我忽然看見幻象:我和小黃在曠野上跑,風掀起我們的毛,像兩團滾動的云。
離別那天,又是一個暴雨如注的日子。我看見他把我掉在他枕頭上的一撮毛,小心放進了錢包。小黃又來院子外等我了,尾巴搖得像朵綻開的花。 我跟著它沖出院子時,沒敢回頭。
小賈,我知道等這里結束,你也會奔赴下一個工地了——你們修通了山海的路,卻總在趕往下一段征途。
這兩年我學會了等,可現在才懂,有些等待是屋檐下的暖,有些奔跑是曠野里的風。你給我的安穩,是這世上最軟的窩,可小黃的尾巴尖,是我沒走完的遠方。
就像《忠犬八公》里說的:“命運早把相遇寫進信里,我們只需順著風走。”我會記得你摸我腦袋時的掌心溫度,記得板房里臺燈下的影子,也會記得此刻風里的青草香。
如果有來生,我想變成人。在某個剛通車的路口遇見你,張開手掌跟你握握手——這次換我說:“你好,小賈。”
來源 | 臨空片區項目 吳相雅編輯 | 黨群工作部 姚詩佳
 客服熱線:
客服熱線: